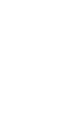垦殖荒芜地 嘉禾献九州——关于教育行政学院第一任院长董纯才的采访札记(徐丽丽)
2021年10月09日
垦殖荒芜地 嘉禾献九州
——关于教育行政学院第一任院长董纯才的采访札记
徐丽丽
 “八十五春秋,笔耕勤不休。垦殖荒芜地,嘉禾献九州。红颜事稼穑,白首犹耕耘。育成新香稻,余热报国心。”这是前国家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教育行政学院(现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一任院长董纯才,1990年85岁寿辰时所写的《八十五书怀》。就在那一年,董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垦殖荒芜地”的开创精神,“白首犹耕耘”的敬业精神依然给人以诸多启示,他所留下的“嘉禾”已然枝繁叶茂,茁壮成长。2005年,恰逢董老一百周年诞辰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五十周年华诞,我们翻阅了大量纪念文集、人物传记,采访了董老的夫人以及同事、朋友,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八十五春秋,笔耕勤不休。垦殖荒芜地,嘉禾献九州。红颜事稼穑,白首犹耕耘。育成新香稻,余热报国心。”这是前国家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教育行政学院(现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一任院长董纯才,1990年85岁寿辰时所写的《八十五书怀》。就在那一年,董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垦殖荒芜地”的开创精神,“白首犹耕耘”的敬业精神依然给人以诸多启示,他所留下的“嘉禾”已然枝繁叶茂,茁壮成长。2005年,恰逢董老一百周年诞辰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五十周年华诞,我们翻阅了大量纪念文集、人物传记,采访了董老的夫人以及同事、朋友,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董老“垦殖荒芜地”的努力先是从1931年追随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参加“科学下嫁运动”,进行科普创作开始的。1932年,董纯才翻译了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的科普读物《几点钟》,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伊林作品。伊林是一位世界级的科普作家,他善于运用散文的笔法,生动有趣的故事,形象具体的描写,既简单明了又引人入胜地讲解科学知识。董纯才还翻译了《不夜天》、《白纸黑字》、《十万个为什么》、《人和山》、《五年计划的故事》等伊林的作品,他的译作信、达、雅,不但在当时受到普遍好评,直到解放后,这六本书还多次再版。董纯才还是中国最早从事科普创作的一代宗师,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科普作品,比较著名的有,三十年代的《麝牛抗敌记》、《凤蝶外传》、《狐狸的故事》等,四十年代的《马兰纸》、《一碗生水的故事》、《人和鼠疫的战争》等,其代表作是《凤蝶外传》和《马兰纸》,细腻生动的笔触,妙趣横生的描写,给这些作品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董纯才不但在自己的科普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而且还不断追求、探索对科普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最早提出在科普作品中要宣传科学精神,是我国科普理论探索的先行者。高士其等作家早先也提出过要在科普中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但明确地把科学精神包括在科普内容之中的提法,最早是由董纯才提出的。
在教育上,董老也作着“垦殖荒芜地”的不懈努力。在延安工作时,负责编写革命根据地学校使用的教材,在东北工作时,提出反对奴化教育,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生产建设服务,东北全境解放后,提倡向苏联学习,以政治教育为主,加强系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建立正规的学校制度;在教育部工作时,注意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1954年发表《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在教育战线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规律,积极促成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打倒“四人帮”后又大力倡议复办中央教科所,并亲自担任所长;首倡“五、四、三”学制改革,多次亲自到辽宁阜新市漳武县四合城中学等地进行调研,了解教育改革试验的情况;率领全国政协教育组、民进中央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组成的教育调查组,到上海、宁波、杭州、常州和南京等地做教育改革的调查,以此为基础向党中央递交《关于教育改革的十点建议》;出版《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等等,董纯才同志在教材建设、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制订、学制改革以及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等方面都做出过突出贡献。此外,在师资培养、教育行政干部的培养培训方面,董纯才同志也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的贡献。
要介绍董老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就不能不提及一本书,《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这本书洋洋几百万字,包括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政策、行政管理、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普通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副主编张腾霄回忆说,这本书是在董老的大力倡议下编成的,可以说,没有董老,就没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董老非常重视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教育经验。他曾经讲过,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同样,新中国教育的创建,也必须在革命根据地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学习苏联教育和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老一辈的教育工作者大都年事已高,有的甚至已经离开了人世,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抢救”这些宝贵的教育经验,使之能够流传后世。他不仅亲自撰写了长篇绪论和经验总结(未完成稿),在第一编(土地革命时期)定稿时,还不顾病痛,将三十万字的书稿审了两遍,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董老的夫人蒋端方同志告诉我们,董老为编写这本书可以说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他那时候简直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已经完全顾不上考虑个人健康问题了。一间十平米左右的书房,一张普通的书桌,一个高倍的放大镜,每天陪伴董老长达十多个小时,这样长时间的辛苦劳作,就是健康人都很难吃得消,更何况一位重病在身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蒋端方给董老准备的救命用的硝酸甘油,常常一两天就不见了,有时半夜醒来,董老书房的灯还在亮着。蒋端方为董老的健康而焦虑不安,但她所唯一能做的,却只是悄悄地把盛硝酸甘油的空盒添满。因为她知道,董老是多么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能给他献出毕生精力的教育事业多留下一些宝贵的经验、让后人能少走一些弯路啊!
1990年,董老心脏病发住进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教育史的编写工作,并口述了一封给张腾霄的信,对编写工作提出了最后的意见:“抗日战争时期是这部分的重点,毛主席在这一时期对教育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因而这一段的方针政策部分一定要写好。”5月21日,张腾霄跟另一位副主编皇甫束玉赶到医院,董老正好一时清醒,目有所视,但口不能言。张腾霄二人对董老说:“您的意见,我们一定照办,努力把这本书编成编好,请您放心吧!”董老点头会意。第二天上午,董老就与世长辞了。说到这里,张腾霄停了下来,他眼神迷蒙,沉默了很久。
张腾霄等人遵照董老的嘱托,终于将《中国革命根据教育史》付梓出版。这是怎样的一本书,董老在生命垂危之时仍记挂着的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教育经验主要是什么呢?仔细研读《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我们读出了这样几个字:“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干部教育”。这也正是董老非常看重的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宝贵经验。
张腾霄同志回忆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有影响力,董老曾是陶行知的学生,追随陶行知作过许多工作,但后来董老在不断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局限。单纯重视实践,轻视理论学习,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正是它的致命弱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教育工作就走出了这一局限,不但非常重视理论学习,而且注意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恩格斯说:“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衡量干部学习的好坏,有无成绩或者成绩的大小,主要不是看他读了多少马列主义的书,记了多少马列主义的条条,而是看他能否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一定要继承、发扬下去。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群众发动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决定革命战争能否取得胜利。要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来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弥补由于大批有经验的干部的牺牲而带来的职位空缺,只能通过干部培训的方式。为此,在整个革命根据地时期,干部教育一直处于教育工作的核心位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促使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在各地迅速形成了干部学习的高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不断扩大,特别是1948年以后,全国大中城市相继解放,需要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到这些新解放区去接管工作,这些干部不仅要学习政治、文化,还要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为顺利完成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干部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干部训练班和干部学校教育三种形式,其中,开办短期训练班是各根据地对干部进行教育训练的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被广泛采用。这种教育形式的特点是:目的明确、短期速成、机动灵活、简而易行。一般学习目的明确,时间较短。在教学内容上,相对于干部学校对理论、专业和文化课程比较系统地讲授,干部训练班更具有针对性。往往是在工作中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开办什么训练班,学习哪一方面的知识。正因为此,训练班可以说使工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由于参加训练班学习的干部,一般是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不存在重新分配或者调离工作的问题,非常简便易行,所以许多领导干部都把办训练班看成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工作需要,就可以马上办个训练班。在教学方法上,许多训练班采用典型报告的方式。因为参加学习的学员大多来自实际工作岗位,而且不少人都是做同一类工作的,所以,往往某个学员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其他许多学员共同遇到的问题。一个人介绍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对其他学员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有时候,训练班还会组织大家去参观访问,这样可以对讲授的内容、方法有更直观的认识,更好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
董纯才1937年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与业务并重、干训为先,这些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深深根植于他的思想深处。董老认为,办好学校,关键在于改进学校领导、提高教师的水平。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就非常重视培养和提高教育干部和教师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于1933年开办教育干部学校,着重训练省、县两级的教育干部。董老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1949年,创办东北教育行政学院,兼任院长,培训东北地区的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和教育厅局的行政干部,开我国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之先河。东北教育行政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校教育领导干部,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董老就任教育部领导工作的1953年,正值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当年中央人民政府的文教方针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小学师资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培养教师。毛主席提示:“教师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执行者,是培养人才的人才,是学校教育的支柱。”于是,董老明确指出:普通教育的整顿和发展,师资是重要的环节。学校领导干部、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中小学办学的多少和好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重视师资建设。战争年代我们党重视教育,不说空话,认识到教育重要就下力气去办。延安时代那么艰苦还办干校,没有战略眼光是不行的。
1955年,董老倡议创办了教育行政学院(现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并兼任院长,培训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师范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的正副校长;教师进修学院的正副院长、教务长;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机关的处长、科长干部和政治教师。他明确提出学院的办学指导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业务并重。为加强学院自身建设,他强调汲取国际经验的重要性,正式聘请了数位苏联专家到校作系统讲授。学员通过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中共党史等课程以及实习和考察,使自己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领导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毕业之后回到各地,大都成为教育行政管理、教育干部培训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骨干。毛主席曾称赞办教育行政学院的方法好,并于1957年在中南海接见了当时在教育行政学院学习的第二期全体学员及教职员工,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
当年在教育行政学院任课的伍棠棣老师回忆了在学院创办初期,董老关心学院建设的一件小事。当时学院刚创办不久,伍棠棣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到学院任教。参训学员大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边听课,边扇扇子、喝水,有的满不在乎地自由进出教室。这给伍棠棣的印象非常不好。更有甚者,有的学员由于基础太差听不懂,要求换教师。对此,伍棠棣非常恼火。师生之间产生了分歧和隔阂,陷入僵持。当时兼任学院院长的董老知道了师生之间的矛盾后,非常重视,他专门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调解纠纷。董老一方面耐心地做学员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又语重心长地劝导伍棠棣,建议通过典型案例来深入浅出地讲解大道理;通过学习骨干带动全班学员互帮互学。经董老点拨,伍棠棣茅塞顿开。经过一个多月的尝试,效果非常很好。对这样小的事情,董老都如此关切,可见他对于教育行政学院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视。
按照教育部的计划和董老的意愿,教育行政学院是要长期办下去的。但这个计划却因康生的干扰破坏而不得不中断。原教育行政学院教师滕纯回忆说,1960年7月,学校已经放暑假了,突然接到通知,说康生要来学院讲话,大家心里都很紧张。康生跑到学院,劈头盖脸地指责在“教育革命”期间(指由1958年“大跃进”引起的“教育革命”),下面在搞阶级斗争,你们把校长们集中到这里学什么教育学、心理学,太脱离政治,要立即停办。当时董老也在场,他的表情很严肃,看得出董老是不赞成停办的。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次董老跟滕纯谈到,一个好端端的教育行政学院被康生一刀砍掉,致使教育干部培训被迫中断了十几年,真是让人惋惜。
回过头来再看董老晚年倾注大量心血,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我们似乎才读懂了这部书,我们仿佛才了解了董老的殷殷期望:教育行政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教师业务水平的进修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与业务并重的原则,大力开展教育系统的干部教育工作。
董老认为,苏联的人造卫星能上天,是因为他们的中小学教育搞得好。所以早在东北工作时期,董老就提出要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尽管当时他就指出,学习苏联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同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相结合,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但在其后几年却因为教条主义的罪名,而招致了有关方面的批评。据上海教育界的老领导吕型伟回忆,大约1958年,中央召开全国文教书记会议,有的同志对教育部学习苏联经验和凯洛夫的《教育学》提出了批评,董老在大会上对此作了说明和自我批评(参见《董纯才纪念集》第140页)。董老的夫人蒋端方介绍说,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董老在向毛主席汇报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情况时,也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接下来,中宣部对董老进行了一个月的党内批判。接着董老也被迫“病休”。文化大革命时期,董老又被拉出来,作为“中国的凯洛夫”挨批斗。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上向“苏联老大哥”一面倒,教育上缺乏办正规教育的经验,学习苏联也是情理之中。而且,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公认有三个最好的时期,50年代就是其中第一个时期。我国现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大批骨干力量,正是那个时期在学校里打下坚实科学知识基础的。
打倒四人帮后,教育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远远落后于教育改革实践的现状,引起了董老的极大关注。1978年,他向党中央建议及早恢复在“十年动乱”中被撤销的教育科研机构。当国务院批准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时,他又欣然接受担任该所所长的重任。在他任职期间,对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研究方法、学风、队伍建设等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他还主编了一本教育科学的重要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这是他对教育学科的一大贡献。
董老创办的教育行政学院(现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历程,学院自1982年复办以来,牢牢把握理论联系实际、政治与业务并重的办学方针,深入开展培训,全面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管理水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领导骨干,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作我国教育系统的“黄埔军校”,现在,全国各地教育系统的上上下下都有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员的身影,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嘉禾”满九州了。饮水思源,我们必须牢记董老当年“垦殖荒芜地”的艰辛与远见卓识,继承并发扬革命根据地时期丰富的教育经验,弘扬传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再铸辉煌,努力办好新时期的教育行政干部培训工作。



 所在位置:
所在位置: